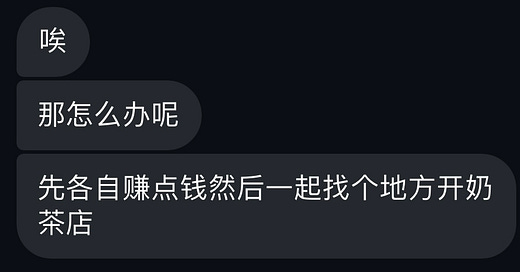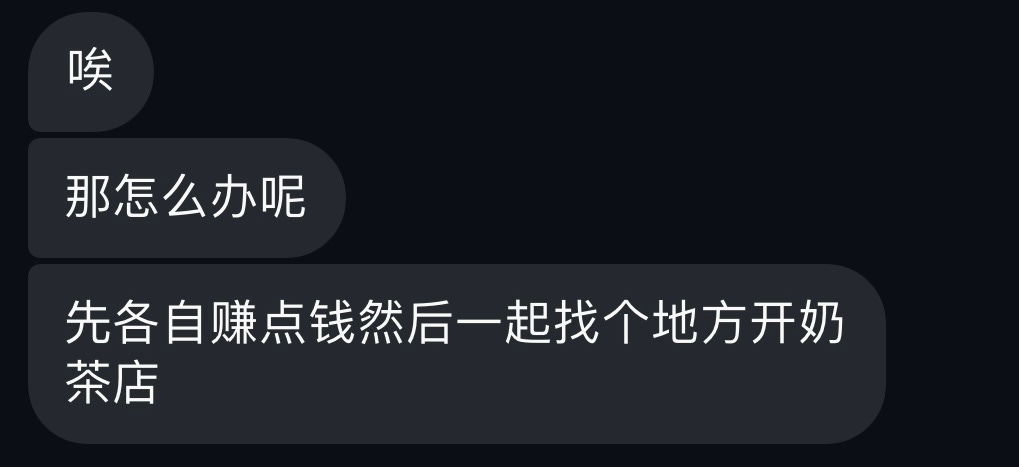没有人能在最后时刻到来前做出选择
我在伦敦打工的餐厅认识的中国朋友S今年底签证到期,上个月她突然说要辞职。其实她来我们这间店也不过三个月,我很诧异,问她原因。
她说她找到了给工签的工作,我带着又嫉妒又好奇的心情继续追问。
她说是一个正在扩张的日料店,想要找一些人培养成店长。但是不在伦敦,在英国中部的一个小镇。
我说不错啊,老板哪里人。
不出所料,中国人啦。
我笑说那你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当一个成功的中国老板,然后回来咱俩开个奶茶店。
过了几天我俩约着出去玩,玩了一整天,吃晚饭还是聊到了这个事情,我才知道最后就算留下当了店长,这个办签证的钱还是得自己出。
我当时心里就梗了一下,感觉不太对,但也没表现出来。
然后她就坐火车去了。
三天之后,我难得的休息日,跟一个姐姐在soho吃了饭,正聊着天往公交站走,手机里弹出消息,“我回伦敦了宝”,我和姐姐道别,上了公交,坐在二楼第一排,眼前是伦敦最漂亮繁华的Regent St.,一低头就是我和S的对话框。用几站地的时间思考了一下该怎么回复,还是傻傻地打出了
“啊?这么快?”。
得到的回复是那边和想象中不一样。
我又发出了下一个愚蠢但也算合理的问题
“回XXX(餐厅名字)吗?”
她说短时间可能不回了。要思考一下未来,可能要回国。
我极力的压抑住了当时就去找她的心情,发讯息说我们可以下周X出来见。
又过了几天,就是今天,又弹出了她的消息“月底之前你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出来”,我吓一跳,我说月底吗,今天不是月底吗,天知道我讲话怎么总是这么笨。好在她的答复是八月底。
她说她要回北京。
我们聊了聊关于中国的事情,关于北京的事情。
我再一次说了
“我一辈子都不想回北京,但是如果你在,我会去找你玩。”
她说没记错的话,公司在二环。
我说那你要不试试住胡同,胡同好玩。
她说(北京的)胡同好玩吗,我还是觉得南方(的城市)好玩。
我说胡同热闹呀,好吃好喝的。
她说你下班会去泡吧吗,你看你在伦敦下班也是回家啊。
我想也没想就说,在国内的话,我还是会去的,在这里不去,只是社会归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和我的社区还没有连接。
她说如果有朋友的话,应该会去,不然下班还是更想回家呆着。
我说你会有新朋友。
接着又补了句,只是你离开伦敦,我会少一个朋友。
她说我也是。紧接着发了句“那怎么办呢?先各自赚点钱然后一起找个地方开奶茶店”
奶茶店。话题竟然拐回去了。面对着手机屏幕的我,一下哭出来。
人生真的是三姐妹和万尼亚。三姐妹心心念念的莫斯科,成了我们所在的伦敦。当然它也是纽约、是巴黎、是北京。我们辛勤工作,然后不断接受、接受、接受,再继续工作。艺考时候读到睡着的本子,七年间,会变成一想到就会哭出来的故事。
比被预言更让我无法平复的,是戛然而止。
太多戛然而止,没有缓冲的结束。
反思这几年,不光是我眼中的别人,别人眼里的我好像也是这样(虽然别人可能没这种感觉,或者更大的时间节点,把我们一对一的戛然而止对冲了)。
就这样吧。
补充一点前情和题外:
在我们这间餐厅打工的几乎所有兼职同事,都是伦敦各大艺术名校毕业的学生或者从事艺术或媒体相关行业的人。做小时工以前,大家的身份是“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编辑”“舞者”“演员”,或者至少是以“UAL”为前缀的XX专业学生。起初大家都只是想找一份解决房租和生活费的工作,然后骑驴找马,看其他机会。或者在下班和休息日做做自己的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得到了更好的机会远走高飞了,但是如果选择继续在餐厅,就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打工到签证结束,离开。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护照是可以一直在这里自由打工的。
二是,深耕在服务业,等一个工签,然后在某间店一直干三年甚至五年。换到卡,再做其他打算。
如果选择了第二条路,同时也意味着,很大概率会失去来到餐厅之前的身份,持续多年过一种平静、规律的打工生活。
没有人能在最后时刻到来前做出选择。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给自己做人生计划,结果计划到快要24岁,突然不知道怎么计划了。可怕的老钟思维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没法接受自己一事无成。喜欢的东西很多,想要尝试的事情也很多,但放在现实面前,就还是要先解决最基本的生存身份和日常开销。今年以前我一直觉得,在餐厅和零售打工是学生时期才会做的事情,结果到了非母语国家,我也接受了它作为最常见不过的谋生手段。
但在这间店短短半年的打工生活,已经让我厌倦了做自我介绍和说再见,也厌倦了日复一日上下班。还记得有个同事,我只和他共事过一天,隔周他就飞走了。偶尔我会想象离开的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会不会反而更舒适。是不是只有我们老钟想要换身份留在这里,是不是别人只是把这几年当作一段丰富人生的经历而已。
写于2024年7月30日夜,伦敦